朱邦芬:黄昆先生之风
作者:朱邦芬,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出处:《物理》2019年第8期
2019年9月2日是黄昆先生百年诞辰。黄先生离开我们已有14年了。
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4年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导师吴大猷),1948年在英国布列斯托尔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导师莫特),之后任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ici博士后研究员,并有一半时间访问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与他合著了《晶格动力学理论》。1951年黄昆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北大复旦等五校联合举办的半导体专门化教研室主任、北大物理系副主任。黄昆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197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iupap半导体分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是:做人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做事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做学问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其中人格高尚是第一位的。我曾在多次演讲中介绍过黄昆先生的科学研究和治学精神,今天先简单回顾黄昆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及治学之道,再简述他为中国科技与教育发展立下的功劳,最后着重谈谈他的为人,以此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辰。
做学问
黄昆科研有两个活跃期。一是在英国的6年(1946—1951) 。期间最重要的科学贡献包括:(1)提出杂质和缺陷引起晶体中的x光漫散射的理论,后来经实验证实,被称为“黄散射”,或“ 黄漫散射”;(2) 理论上为电子气屏蔽的“friedel 振荡”打下基础;(3)提出一对唯像方程描述长波长极限时极性晶体中光学声子位移、宏观电场与电极化强度三个物理量的关系,被命名为“黄方程”或“玻恩—黄方程”;(4)提出晶体中的电磁波与晶格振动格波的横波会互相耦合,形成新的本征模式——声子极化激元,一种新的元激发;(5)建立在晶格弛豫基础上的多声子光跃迁与无辐射跃迁理论——“ 黄—rhys 理论”(rhys 即黄昆夫人,中文名李爱扶),成为固体杂质缺陷束缚电子态跃迁理论的基石;(6)与玻恩共同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专著。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国际固体物理学界和晶格动力学领域的一位领头科学家。1977年至1990年黄昆迎来了研究生涯的第二个高峰。主要成果有:(1)统一了3种不同的理论模型,解决了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的疑难问题;(2)建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的“黄—朱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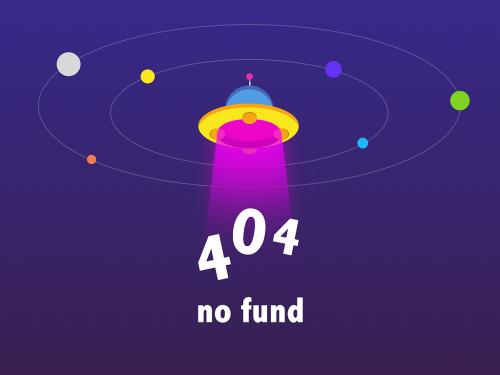
上述黄昆8项主要的科学贡献,除x光漫散射理论和“friedel振荡”外,都与量子化的晶格振动格波,即与声子有关,主要研究对象是声子和声子参与的固体光学或电学等物理过程。即使x光漫散射理论,也与晶格的非完整性有关。因此,黄昆曾多次谈起,他一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声子物理。毫无疑问,玻恩是晶格动力学的奠基人,但是在用量子力学重新系统阐述晶格动力学理论方面,在进一步研究声子参与的固体中各种物理过程,在声子物理学科的开拓方面,黄昆是国际最主要的开创人之一。为此,我曾用“声子物理第一人”作为黄昆传(国家最高奖获得人丛书之一)的书名,得到黄先生的认可。
黄昆在60年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形成了极具鲜明特色的个人风格。黄昆的治学,如同他的为人,朴实、低调。他的名言,“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充分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和朴实的风格。黄昆把自己一辈子的科学研究经验归结为“三个善于”,即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发人深省。
做事
黄昆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其一,黄昆是公认的我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两个学科的开创人之一,特别是新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开创人之一。他参与制定了中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1956—1967年),为重点发展我国半导体事业提出了具体规划及实施的紧急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要尽快培养半导体专门人才。之后不久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有关教师,四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从1956年暑假起集中到北京大学,开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还包括南开大学及清华大学本科生和旁听生20名)。专门化培训班由黄昆任主任,复旦大学谢希德任副主任,集中在一起的教师近30人。两年内,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建设了一系列从理论到实验的半导体专业课程,培养的二百余名学生,成为我国半导体事业的“黄埔一期”。1977年11月,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黄昆从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担任了6年所长,而后一直是名誉所长,他对提升半导体所的学术水准有着突出的贡献。黄昆是一位有远见的半导体物理的学术带头人。他很早就觉察到,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作为半导体物理、材料与器件三者结合点,有可能成为半导体科学技术一个重大的发展, 为此他团结全国相关力量,领头筹建超晶格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在这个新兴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

虽然自己不研制半导体芯片,黄昆对我国半导体微电子产业的历程认真作了反思。除国内政治干扰和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等原因外,除国内多部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分散强度低、基础材料、工艺水平不过关、不重视产品的成品率和开拓市场等管理问题外,黄昆总结出一条教训:越是国家重视的学科,该学科的基础科学研究反而越容易受到冲击。1950年代的金属、1960年代的半导体,都是国家十分重视的学科。中国科学院集中全国精兵强将分别成立了金属研究所与半导体研究所,为国家的“以钢为纲”和“电子技术革命”战略打基础。但是回过头来看,由于急功近利,作为学科基础的金属物理与半导体物理的研究,相对而言,长期以来却是受冲击最大的学科。这是因为,对于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物理研究往往“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政治运动来了以后却常常首当其冲,动辄就被扣上一顶“脱离实际”的帽子。这样,刚起步时我们和国外研究水准相差不多,但由于不重视自己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导致差距越来越大。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黄昆总结的这一规律值得我们引以为训。
黄昆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长期在第一线从事物理教学,为一代又一代物理学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教育是国家科学技术腾飞的基础,黄昆始终认为,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队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北京大学那些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上。1978年初,黄昆任半导体所所长不久,每星期抽半天系统地为大家讲授现代半导体理论,帮助全所科研人员在大学本科所学的半导体物理和研究一线所需的半导体物理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一连讲了10个月。黄昆把教学当作科学研究,精心钻研教学内容和方法。他讲课概念清晰,深入浅出,是有口皆碑的教学名师。
做人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我认为,把这两段话用于黄昆先生,也是完全合适的。我和黄昆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达15年之久,几乎每天都跟他讨论问题,无拘无束,有幸成为世上受他教诲最多的一个人。黄昆先生生前,我撰写过他的小传,参与编过他的70寿辰纪念文集 和纪念85寿辰的“黄昆文集”,编过他的“selected papers with commentary”。黄先生逝世后我也写过若干文章,包括评论他的经典著作,回忆他的教书育人,也曾就他1947年给杨振宁先生一封长信写过感想。离开黄先生越久,我越钦佩他的意志纯洁、公正不阿、珍惜国家科研经费、极端谦虚、学风纯正、严于律己、在任何时候的公仆意识,而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些品质尤为我国科教界当前所欠缺和急需的。
1、意志纯洁
黄昆在1947年给挚友杨振宁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杨振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实验做得很不顺利,而原来自视甚高的他产生了disillusion的感觉。黄昆的信主要是鼓励杨振宁,说“successfully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nobel prize还高”,信中还有一句话:“devotion to the cause 的心也一定要驾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这实际上也是黄昆的信念和自勉。
在信中黄昆探讨了当时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回国,还是暂不回国?一方面,“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这是一句可以与王淦昌先生“我愿以身许国”和彭桓武先生“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相媲美的名言,反映了中国老一代科学家救亡强国的精神。有此“一般维持思想的力量”,才使得他们区别于来自其他殖民地国家的留学生,才不等同于“高级技师”。这封信很有深意,充分反映了黄昆的献身精神、意志之纯洁和坚定。
事实上,黄昆也是这样做的。黄昆1951年底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上没有继续从事他原先在英国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成就奖后,媒体记者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你没把研究工作长期搞下来,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黄昆并不赞同这一说法,“因为回国后全力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一个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 他还说,他是把教学当成科研来钻研,在教学中研究了很多问题,自己在教学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黄昆带出了一大批学生,他们成为了中国半导体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骨干,他觉得自己教学的贡献并不比做科研的贡献来得小。其实,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当年回国也都抱着献身事业的雄心,如叶企孙“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学术独立”,华罗庚、钱三强等回国也旨在为中国数学、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尽管对个人的科研成就带来一些影响。
2、公正不阿
目前,国内科学技术界强调竞争,这对择优支持有积极意义。但是,一种不好的风气也在蔓延。许多学界领袖,包括众多院士、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过多地考虑本单位和本人所在的研究领域的利益,常置大局不顾,很少从全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平衡发展而考虑问题。黄昆总是从全局利益和学科合理的布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从不为本单位、本部门谋取不合理的科研经费和设备,不为自己熟悉的人争取不恰当的利益。他曾说,跟他关系越密切的单位,跟他关系越密切的个人要吃点亏,因为他首先要考虑那些他不熟悉的领域和个人。夏建白是黄昆的研究生,又是半导体研究所理论研究组的组长,他曾向老师抱怨,国家攀登计划中,理论组分到的钱太少了,而理论组的贡献最大,然而这并不起什么作用。黄昆曾担任国家“八五”攀登项目的首席专家,他汇集全国所有从事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研究的单位和个人,共谋发展,公平分配研究经费,而不是半导体所一家独大。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这种境界。
黄昆评价一个人难免会有偏差,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bias。但是,他不以被评人与自己关系亲疏为转移,尽可能公平,丝毫没有国内某些人的门户之见,不为本单位、小团体争利益。他很少给人写推荐信,一旦要写,他都亲自动笔,意见尽可能客观,既不夸大,也不蓄意贬低。20世纪80年代,经常有人请黄昆评奖,审查书稿,审阅研究生论文,后来发现,黄昆的评审意见总是不留情面,于是请他的人越来越少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工作在学术上的意义吹得过高,黄昆毫不留情地在评审意见上指出这是学风问题,并很不客气地写道,导师应引起注意,加强对学生教育。北大是黄昆长期工作的地方,尽管他对北大很有感情,但爱之愈深,责之愈严。
3、珍惜科学研究经费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黄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特别珍惜国家的科学研究经费。他这辈子只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是1986年从半导体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他带领理论组11位研究人员,申请一个面上项目(为期3年),共2万块钱。这项基金项目完成得极好,出了多项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在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这个新兴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担任所长期间,由于国家重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下拨到研究所的经费比较多。每当国家科委下拨大笔经费到半导体所时,他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这四个字是黄昆自己写的)。尽管这些经费不是黄昆自己用,而是研制器件和材料的研究室用,但他唯恐经费用得不合适,没做出预定的成果,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的血汗钱。他经常说,“基础研究,也应算一算投入产出, 算一算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现在有的人明知道自己的项目在学术上或在应用上都没有太大意义,不值得国家投入大笔经费,却以“不要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为借口,宣扬“钱花在科研上,不管怎么花,总比贪官贪污要好”,千方百计套取国家的经费,摊子铺得很大,以量取胜。我想黄先生如果还在,绝不会赞同这种做法。当年他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再做出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他对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昂贵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很不以为然。他的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地在科学上作出贡献。”有的人把国家的钱不当钱,大手大脚浪费国家的科研经费,而对自己腰包里的钱精打细算;黄昆恰恰相反,特别珍惜国家的经费,对自己的钱却不太在乎。
4、极端谦虚
黄昆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以后,面对一些媒体的采访,他经常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他又说“我这一路走过来非常幸运,每个时期都是有着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即使在1951年至1977年期间,他在北大几乎没有从事科研的机会,但是他觉得自己在教学中培养了一批人才,同样能把个人的才能发挥出来,也是命运给他的机遇。
黄昆的谦虚常捎带一点儿俏皮和自嘲。例如,回顾求学生涯,黄昆多次说到自己的中文不够好,耽误了很多事情:“我的语文基础没有打好,多少年来,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都给我带来不小的牵累(从早年的考试到以后的写作,以至讲话发言)。近年来,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其实,黄昆虽然称不上演说家,但除非念稿子,他的讲话言之有物,没有八股味,而且很幽默;而他的中文文章虽短于抒情和描写,有时会带一些英文句式结构的痕迹,但条理清楚,论证严密,非常注意句子之间、段落之间和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句式表达十分有力,具有科技论文的典型风格。他偶尔对个别字的写法拿不准,自嘲为“容易接受菜场和食堂的新发明的简体字”。
5、学风纯正
黄昆在学术诚信方面为我们树立了高标准的典范。他不仅不争个人名利,而且有些他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成果,只要他觉得自己的贡献没有超过一个阈值,他就拒绝署名。
“多量子阱系统中光学声子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研究工作,黄昆与我各用一种方法做了推导,两者结果一致,然后由黄昆撰写成文,论文一共40多页,都是黄昆在家中用他的打字机逐字逐句敲出来的。黄昆在撰写论文时,把我作为第一作者,自己名字放在最后(当时在凝聚态物理研究圈子中并不流行通讯作者的概念),他认为这项研究是由我提出的问题,并做了主要的理论推导。另一方面,鉴于论文主要是黄昆起草的,他也作了主要的理论推导,最后由我投稿时我还是将黄昆先生列为第一作者。
“超晶格中的光学声子”这篇文章,是我基于黄昆1950年的“偶极振子”模型开展研究的。研究中我们多次讨论,我起草成文后黄昆先生又多次仔细修改我的文章。因此在文章中我把黄先生也列为共同作者,但他认为主要研究是我做的,修改时断然在自己名字上打了个大叉,拒绝署名。
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所有一项科研项目“砷化镓中氮及氮—氮对束缚激子的压力行为”,实验和理论都是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做的,特别是理论研究,主要是他指导研究生做的。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好,作为1985年半导体所成果上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但是,黄昆自始至终坚持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获奖人名录中。
黄昆先生一生发表研究论文约40篇左右,但是每篇文章都实实在在解决了某个物理问题,他不赞成“灌水”。20世纪90年代,有的人一年能发表十几篇论文,他在觉得这些人“了不起”的同时,又对文章的含金量表示怀疑,因为他留英6年全时做研究,共发表了13篇论文,这在当时属于非常高产,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尽了全力的。当然到了21世纪,我们有的人“灌水”就更厉害了!
黄昆做研究的特点是事必躬亲。他做研究不是出个题目让学生去做,自己参与讨论,而是一定要亲自动手去做。他体会自己亲手做,会不断有新的想法冒出来。这反映了他的学风纯正。
黄昆做研究不喜欢随大流,他当所长也有自己的准则和底线。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一些机关单位滥发钱物,所里常有人以“别的单位如何如何”劝说黄昆放弃一些原则做法,黄昆对于这种“法不责众”的随众心理和做法很不以为然。在一次所务会议上,一位同志建议应当想办法为群众“谋福利”,说“太老实了,要吃亏”,黄昆听了笑笑说,“还是老实点好,如果一次不老实,将来会有很多次不老实”。
6、严于律己
黄昆在“文革”以前,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思想倾向,一直比较左。但是他的“左”应该说是出自内心的,更多的表现在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上。例如,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按规定可以定级为“一级教授”,但黄昆主动要求将自己定为“二级教授”,觉得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文革”以后,黄昆政治上有所觉悟,不再那么左了,但律己照样极严。例如,“文革”后补发工资,他把两万元全部都交了党费。黄昆从不领取出国的制装费和补助费,大量国内外工作信函的邮资全都自己支付,因私事不得不打电话和用车时,必定交费,等等。1984年,黄昆作为“斯诺教授”访美。他省吃俭用,将外方资助生活费节余的钱购买了一台全自动幻灯机及调压器,为半导体所对外学术交流之用。1986年2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固体物理研究所举办庆祝弗洛利希80寿辰学术会议,邀请黄昆参加,并提供他500马克生活费。结果,黄昆把结余的近400马克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供所外事同志工作用。
黄昆不光严于律已,而且对他的英裔夫人李爱扶要求也极严。按说李爱扶是英国bristol大学物理本科毕业的,但是她在北大物理系长期担任普通实验员。黄昆刚当半导体所所长时,所里亟需一位英语口语教师,有人提议把李爱扶从北大调来,因为她是一位理想的英语教师。但是,黄昆坚决反对亲属在自己领导下工作,认为至少应该避嫌。1987年他应邀去广州参加第6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因为李爱扶来中国三十多年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黄昆决定乘开会之际,顺便陪她去广州看看。按说黄昆的旅费由公家报销,而李爱扶的旅费由自己出,这是律已的做法;但是,黄昆以自己未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为理由,他的往返机票费用也完全自付。

黄昆夫妇生活上特别易于满足现状,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的生活有了根本变化,可是黄昆家的生活没有与时俱进。家里除了墙上新装的一个空调、一台普通的25英吋彩色电视机、一台老式的组合音响以及许许多多的唱片和录像带外,没有太多现代化的东西。黄昆家是一套70平米小三室的单元房,建于1955年,楼刚刚盖好,他们就搬进去了,一直住到21世纪。简单的水泥地砖,没有任何铺设。大间房间的面积约18平米,是他们的客厅、卧室兼黄昆的办公室。房间很挤,放着一张双人床、两个简易沙发、一个油漆早已斑驳脱落的旧写字台和两个小书架。黄昆家中的“自由”空间狭小,每次我去黄先生家里,坐在简易沙发上时,李先生就坐在黄昆写字桌旁的椅子上。当客人多于俩人时,他们的床上就得坐人了。有段时间,为了接待几位留英老同学来家里聚会,他们想方设法,把双人床的四个腿用木板垫上,木板下面安上滚轮,客人来时,把床推到一边,腾出待客的地方。当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仍住在50年代修建的狭小而陈旧的房子中时,李爱扶总用她那略带英国口音的普通话说:“只要我们住着舒服就行。”他们对饮食很不讲究。90年代,李爱扶开始比较注意黄昆的营养,每顿正餐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荤菜常常是烧一锅红烧肉,吃上几天。汤经常是西式的素菜浓汤,把土豆、胡罗卜等用食品加工机搅碎,加上西红柿等熬汤。酱豆腐是李爱扶吃饭的“保留菜”,菜不够时就吃酱豆腐。
7、强烈的“公仆”意识
1977年黄昆当半导体所所长第一天上任时,被传达室大爷拒之门外。老大爷尽管知道今天新所长要来,但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位拎着行李,穿着一身颜色泛白的旧中山装,骑着30年“高龄”旧自行车的毫不起眼的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昆。黄昆只得耐心解释,因为是第一天来所上班,他还没有从所里领到工作证。半导体所在皇城根时,黄昆与林兰英、王守武三位所长挤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办公。每天早上一上班,他们一起拖地,擦桌子,打扫卫生,拿热水瓶打开水。1986年半导体所搬到林业大学,办公条件明显改善,然而黄昆办公室还是3个人,除了他,还有我和王炳燊(有段时间是汤蕙)(图8)。当所长时,黄昆中午都在所职工食堂里排队买饭吃。1986年以后,因身体不好而食堂菜太油腻,他便自己带饭,到中午,用开水烫一烫冷饭就吃上了。所行政处要为他解决中午蒸饭问题,被他一口谢绝。
范仲淹用“云山苍苍,江山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赞美严子陵。黄昆先生之风,比山高比水长,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天追思黄昆先生,越发觉得爱因斯坦的“第一流科学家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句话的深刻,值得我们每位科学工作者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也许达不到黄昆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高度,但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他的精神,特别要学习他的公正不阿、大局观和全局观、严于律己、当老实人做老实事等品质,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继承的黄昆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

诵读人:宋毅 中国科学院朗诵艺术团成员